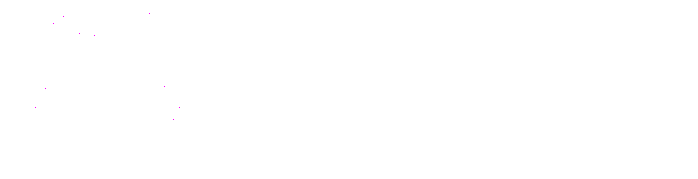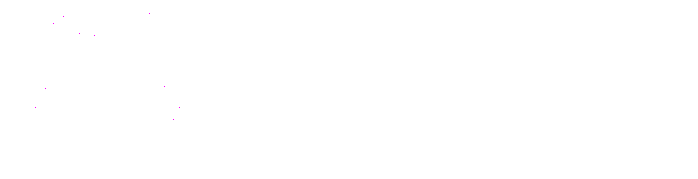一、经济史学与经济学
早在80多年前,国际经济史学界就已对“什么是经济史学”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938年,有人向时任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的历史学家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Temperley)问及“什么是经济史?”这个问题,田波烈的回答是:“根本没有经济史这样一回事”。到了1988年,科尔曼(D. C. Coleman)、弗劳德(R.Floud)、巴克(T. C. Barker)、丹顿(M. J. Daunton)、克拉夫茨(N. F. R. Crafts)等学者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场讨论的主持人科尔曼说,给经济史杜撰一些简单的定义并不困难,但只能是有害无益。如果认为经济史是对过去的社会经济诸方面的研究,是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经济使用的历史,或者认为是对过去经济活动情况的考察,那就太容易了。各种不同的见解都揭示出一种定义,该定义一度被简单地概括为经济史就是要求对经济有一个了解的历史。
“经济史”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两个相关的概念,一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实践、经济表现),二是研究这些活动的学问。简单地说,通常说的“经济史”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经济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的经济,另一个则是研究经济的历史或者历史上的经济的学问,也就是经济史学。
经济史学和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通用的“经济”一词,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定义为“一个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领域”。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人们为取得衣食住行产品以求生存而进行的活动。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对此做过一个总结:“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经济学研究的是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的过程——为社会提供物质福利的过程。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确保日常生计”。为确保日常生计而进行的活动就是经济实践,而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为了了解这些规律,就必须了解历史,诺斯(Douglass North)对此做了很经典的说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未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因此,研究现今经济实践的学问是经济学,而研究过去经济实践的学问就是经济史学。二者都研究经济实践这一客观存在,差别只是这个客观存在的时间不同而已,因此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希克斯(John Hicks)在1942年出版的经济学入门书中,就把经济史学与应用经济学等同起来。当然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因此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中说:“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
二、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史学
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经济活动,而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后,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需要用专门的技艺来进行管理。关于这种专门的技艺的学问,就是经济学。
今天中文中的“经济”一词,译自英文的“economy”。英文中的economy一词,又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家政术)。古希腊人色诺芬的《经济学》(Οἰκονομικός)一书是西方保留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有关于经济的著作,讲的是农业生产和家政管理。直到17、18世纪,西方文献中的经济概念主要还是局限于家庭范围,甚至在19世纪,大部分辞书中的“经济”词条,其首要义项依然是“家政”和“家庭管理”。由于农业是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产业,因此家政学也往往主要谈农业经营。
中国西汉晚期出现的《氾胜之书》是东亚最早的农书。《氾胜之书》与古罗马学者加图的《农业志》都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两者都是综合性农书,所谈的方法有不少相似之处,基本思想也是颇为类似。在此之后,中国历朝出现了大量的农书。它们所体现的经济内容,和西方家政学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家政学。
家政学是关于私人对经济进行经营管理的学问。但是世界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国家的出现。尽管国家的规模、形式和性质多种多样,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是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赋税收入。管理赋税的征收、支出和贮备机构和制度就是财政。财政是政府“理财之政”,国家选择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货币),获取一部分国民收入,以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行为。因此,财政是一种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在传统时代,因为国家也对经济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家政学之外还有国家管理经济的学问。这种学问在中国就是“食货学”。
在近代以前的西欧和中国,无论国家治理还是私人经营活动都离不开经济数据。为了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发展出了出现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技巧和工具。在此基础上,近代早期的英国出现了运用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派——政治算术学派。这里的“政治”指政治经济学,而“算术”指统计方法。该学派得名于其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代表作《政治算术》。马克思称威廉·配第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书中运用统计方法对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国情国力作了对比分析。在德国,也出现了国势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康令(H. Conring,1606—1681)和阿亨华尔(G. Achenwall,1719—1772)。康令在大学里开设“国势学”课程。国势学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记录的“城邦纪要”,主要记录各邦国历史、公共行政、文学艺术、科技和宗教等,随后演变为“国情纪要”。康令将其改名为“国势学”。
在中国,至迟从秦代就开始,历代国家都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本地户口、田地、赋税、劳役、治安、地方开支等的数据收集、整理和统计工作。各地上报来的数据由朝廷的财政部门编成诸如《元和国计簿》《万历会计录》一类的大型财政文献。后来的史官或者史家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考证、取舍和编排,加工成《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大型“通书”以及各地地方志中的“食货”“户口”“田亩”“赋税”等部分。这种为国家治理收集、整理经济数据,以此为基础编制相关文献的工作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食货学”。“食货学”以相应的统计组织、统计法规、统计活动、统计制度与方法为基础,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财政学。
政治算术、国势学、食货学这些学问都有几个重要特点:重视经济活动的数量表现;以统计手段为基础;为国家治理服务;等等。这些学问都为经济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成为经济学的先驱。依靠这些学问提供资料(包括经济数据)和方法去研究更早时期的经济情况的学问,就是经济史学的源头。
三、亚当•斯密对经济史学的贡献
经济史学首先出现在欧洲。在西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经济史学的开创之作。
希克斯和海尔布罗纳总结说:回溯所有历史,人类成功地解决生产及分配问题的方式只有三种,它们单独地或结合在一起使人类能够解决经济挑战。这些制度即习俗经济(Custom Economy)、指令经济(Command economy)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用习俗和指令来解决问题,简单明了,但是让每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让社会存续的道理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假如不靠习俗和指令,社会上的所有工作(不论低贱还是高尚),未必都会被完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欧在18世纪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的人,即经济学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国富论》首次明晰地揭示出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制,即一个不靠习俗和指令的社会必须组成一个系统,以确保能生产出生存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必须安排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靠市场。因此,《国富论》从分工开始,系统论述了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社会资本再生产等基本经济理论和运动规律。
严格地说,《国富论》并非一部“原创性”的著作,而是一个时代最优秀经济思想的结晶。洛克、斯图尔特、曼德维尔、配第、康替龙、杜尔哥、魁奈和休谟等一连串在亚当·斯密之前的观察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与斯密很接近,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作者超过100人。然而他人只是厘清了个别议题,亚当·斯密在汲取他人思想的基础上阐明了全貌。
作为苏格兰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亚当·斯密对历史非常熟悉。他和好友,同为苏格兰历史学派成员的休谟、弗格森相继出版了《英国史》和《市民社会史》等名著。斯密本人在《国富论》中也充分展开了其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休谟、弗格森相比,斯密历史性思维的特点在于首次介入了独立的经济生活的领域。斯密认为,经济生活的线索已不再只是一种政治发展史的陪衬,而已经展开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生活研究的理论平台。相比而言,斯密的贡献更大。
《国富论》中谈到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坎南为该书所编纂的索引中,仅字母A的条目中有关历史的就有十余条,如: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在该王朝统治时期繁荣昌盛;亚伯拉罕,称过钱的重量;阿比西尼亚,以盐为货币;公开表演的演员,因为从事这一行受到轻视而领取补偿;非洲,掌握大权的国王还远远比不上欧洲的农人;酒馆,其数量并非造成酒醉的充分原因;大使,他们被任命的最初动机;美洲(其下有一整页参考条目);学徒资格,对这种奴役本质的解释;阿拉伯人,他们支持战争的方式;军队,君王对抗一位心怀不满的教士时,并不安全……
《国富论》中关于历史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引用历史作为例子进行理论分析,例如自然条件、分工、利率、职业培训(学徒);其次,直接讨论历史,例如货币、殖民地;最后,讨论当时的情况,这对后人来说就是经济史。特别是在《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和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亚当·斯密分别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在经济思想上出现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进行了分析,说明它们在经济政策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上不利于经济自由发展的作用,这实际也是为论证如何增加财富而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的论述总结。《国富论》的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论述了为保证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所需要的国家赋税政策,说明了国家课税的必要性,以及课税必须遵循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原则,否则就不利于财富增长。
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是经济史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斯密不仅是古典经济学之父,而且也是经济史学之父。在经济学方面,无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都可以说渊源于亚当·斯密。斯密对经济史学的贡献也为后人继承。柯亨(G. A. Cohen)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不论是对经济学理论,还是对经济史而言,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四、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史学
19世纪后期经济史学开始形成时,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尚未分家。最早的经济学课程是坎宁汉(William Cunningham)1882年在剑桥大学开设的,课程名称就叫“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因此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共享着相同的话语体系。之后,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也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兴、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的兴起,都为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带来了新的成分。但是经济学的主要学派不论彼此之间分歧多大,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赖以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话语体系,仍然是由亚当•斯密创立,之后又经过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人加以发展。与经济学有同源的经济史学,也采用了这个话语体系。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经济史学界,虽然百花齐放,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不断涌现,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仍然是亚当·斯密开创的。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清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有众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不同的学者参加的论战得以持续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采用了共同话语体系——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而后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食货》半月刊两个主要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史研究,也都基本上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包括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是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来源。
到20世纪后期,情况仍然如此。黄宗智(Philip Huang)在《中国经济史中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一文中,对中国和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即规范认识)进行了总结,指出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一些学者也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不是停滞的,而是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学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一些学者侧重于研究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把19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
在西方,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但其主要内容却出人意料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么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他们把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
黄宗智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这一点并不奇怪,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所言:“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除此之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还直接谈到中国,认为中国的国家财富在很久之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制所允许的限度。如果中国改变其法制,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发展限度可能会提高。如果一个国家忽视甚至鄙视对外贸易,或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其一两个港口,那么其商贸是不会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富商或者大财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但是贫民或者小商贩非但没有安全,其财物随时都有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法为借口而被强行掠夺。所以,在中国不能按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进行充分投资。而且,中国还存在压迫贫民、形成富商垄断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富商获得巨额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率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肯定足够负担如此高的利息。他的这些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
原刊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转载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微信公众号。